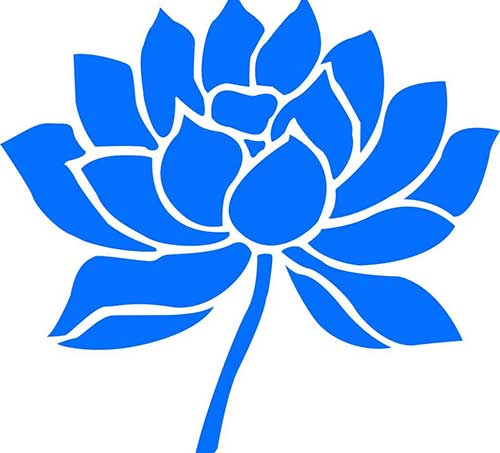侠的文化存在,墨家的推波助澜
发布时间:2022-10-25 09:12:29作者:普贤行愿品常识网
侠的文化存在,墨家的推波助澜
侠的活跃引起了社会的振荡,这一振荡在当时生气勃勃的思想界迅速得到了反响,这便是墨家对于武侠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他们的活动与主张,为侠的诞生和生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墨家”之称得自它的宗师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他的生卒年,据孙冶让考证,当在公元前486年至公元前376年间,大约为春秋未战国初人。他曾自称“贱人”,可见他出身于社会下层。墨家的“墨”字与“黑”等字同音假借,当为后来平民的称呼——“黔首”、“黎民”之初义,说明这一学派的成员来自生活于平民社会中的“游士”。
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为锯子,锯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矩子的指挥。据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们平时一律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制的“歧矫”,是一群深为战乱所苦、决心在艰苦的生活方式和严密的准宗教团体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游士”。
墨家又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所以,墨家并非如同有的学者认为的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
过分严密的组织并不适宜于具有自由意志、主张人格平等的游侠,何况墨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绝非“重气轻命”的武侠所能为之。
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于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
“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在《墨子·经说上》中,墨子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句话,谭戒甫的译文为:“千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放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墨子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闻述,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在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文人的理论学派能够直接对于活跃于民间的武侠阶层进行理论指导的,尚不多见。可见,墨者对于武侠的出现是充满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武侠的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骆滑禽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
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宇里行间,隐隐约约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同时,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由于墨家对侠的理解与同情,因而有些墨者也仿照侠的行为方式处世行事。《吕氏春秋·尚德》中叙述了一个关于墨者矩子的故事。墨者钜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往根深,阳城君便拜托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弟子徐弱极力劝阻,认为死之无益。盂胜回答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于是徐弱出于死节之义,先行撞死于老师面前。嗣后,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83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一方面表明侠的某些行为准则也在影响着社会的其他一部分人:
不但在诸子百家之间,而且在侠所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另一方面,它也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同情武侠的墨家,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是与武侠大异其趣的。孟胜及其弟子虽仿照“重交轻命”的侠义准则行事,们其出发点仍在于“行墨者之义”——即上层文化的“严师”、“贤友”、“良臣”之义。墨家主张通过“兼爱”、“非攻”而不是“锄强助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具体行动上力主“献贤进士”而非“以武犯禁”,这都是与侠的精神乖连的。
墨家的学说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甚至被称为“世之显学”,其门徒“显荣于天下众矣,不可胜数”。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墨家”之称得自它的宗师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他的生卒年,据孙冶让考证,当在公元前486年至公元前376年间,大约为春秋未战国初人。他曾自称“贱人”,可见他出身于社会下层。墨家的“墨”字与“黑”等字同音假借,当为后来平民的称呼——“黔首”、“黎民”之初义,说明这一学派的成员来自生活于平民社会中的“游士”。
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为锯子,锯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矩子的指挥。据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们平时一律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制的“歧矫”,是一群深为战乱所苦、决心在艰苦的生活方式和严密的准宗教团体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游士”。
墨家又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所以,墨家并非如同有的学者认为的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
过分严密的组织并不适宜于具有自由意志、主张人格平等的游侠,何况墨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绝非“重气轻命”的武侠所能为之。
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于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
“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在《墨子·经说上》中,墨子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句话,谭戒甫的译文为:“千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放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墨子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闻述,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在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文人的理论学派能够直接对于活跃于民间的武侠阶层进行理论指导的,尚不多见。可见,墨者对于武侠的出现是充满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武侠的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骆滑禽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
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宇里行间,隐隐约约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同时,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由于墨家对侠的理解与同情,因而有些墨者也仿照侠的行为方式处世行事。《吕氏春秋·尚德》中叙述了一个关于墨者矩子的故事。墨者钜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往根深,阳城君便拜托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弟子徐弱极力劝阻,认为死之无益。盂胜回答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于是徐弱出于死节之义,先行撞死于老师面前。嗣后,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83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一方面表明侠的某些行为准则也在影响着社会的其他一部分人:
不但在诸子百家之间,而且在侠所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另一方面,它也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同情武侠的墨家,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是与武侠大异其趣的。孟胜及其弟子虽仿照“重交轻命”的侠义准则行事,们其出发点仍在于“行墨者之义”——即上层文化的“严师”、“贤友”、“良臣”之义。墨家主张通过“兼爱”、“非攻”而不是“锄强助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具体行动上力主“献贤进士”而非“以武犯禁”,这都是与侠的精神乖连的。
墨家的学说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甚至被称为“世之显学”,其门徒“显荣于天下众矣,不可胜数”。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